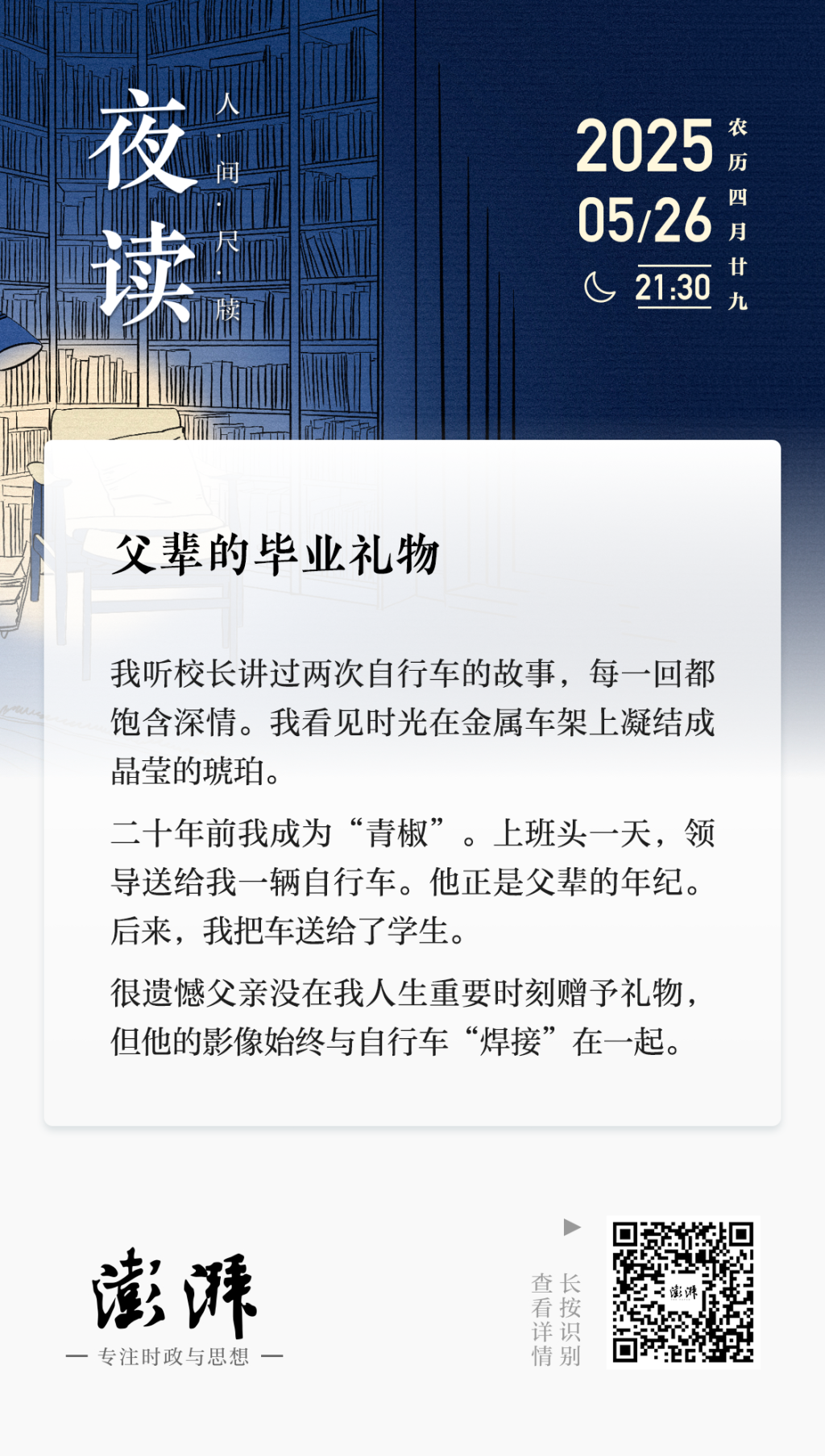夜读丨父辈的毕业礼物
又是一年毕业季。今天,一个大学生在离开学校时,会收到或希望收到什么样的毕业礼物?一个称心如意的升学机会或工作offer,一次特别的毕业旅行,抑或来自母校的定制版文创纪念品?

上海产凤凰牌自行车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“那是1986年,我收到的毕业礼是一辆上海凤凰牌自行车。”校长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,“当时我在上海的伯父凭票才买到这辆‘二八大杠’,真是令我印象深刻啊,花费了180元。我的父亲出资了1/3,伯父出了2/3,并托人从上海运到了老家安庆。”
之后,这辆自行车载着他的主人又从安庆辗转到芜湖,并在1994年回到了上海。“那时候我考取了华东师大的博士研究生,已经成了家。这辆自行车几乎成为了我们一家人的代步工具。我的太太坐在车后座,年幼的女儿则坐在前面横梁上,每天早晨我送她们去上班上学。”
我听校长讲过两次这个故事,每一回都饱含深情。一次是在某次论坛上,校长以上海凤凰自行车为例进行了即兴演讲;最近一次是在与学生“面对面”时,我在现场聆听了这个故事。
我觉得,这份来自父辈的礼物,多少会给年轻人带来启发——尤其是当人们喟叹“从前车马慢”时,从老物件上拾得了多少真挚情感。
如今社会变迁,我们追求日新月异,莫说是自行车了,就连智能手机往往也难逃“年年换新”的消费浪潮。可当校长在回忆里抚摸那辆漆面斑驳的老旧自行车时,我分明看见了时光在金属车架上凝结成晶莹的琥珀——车铃铛里藏着女儿银铃般的笑声,后座垫上还留着太太环抱的温度;早已泄气的车轮,不知驶过了多少个寒暑春秋。那个青年教师,也终成为所属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和教授。
我决定还校长一个关于自行车的故事: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,陪同学来到这所郊区的学校面试。巧了,世上总是上演“无心插柳”的传奇,同学未受垂青,我却最终被录用,成为一名“青椒”。那时候的大学城略显冷清,交通不便,从办公室走到教师公寓有很长一段距离。我们办公室的领导亦是我的伯乐,是他一个电话把我招进学校的。上班头一天,他从仓库里取来一辆自行车送给了我,尽管是女式的。
伯乐头发有些花白,幽默健谈,正是我父辈的年纪。那辆自行车是崭新的,价值180块,保护膜都没来得及撕,原本是他留着自用的。“没有脚踏车,跑学院送个材料都不方便”,伯乐很爽气地说道,“小伙子,这车就当作初入职场的见面礼,送你了!”这让我想起电影《十七岁的单车》里那个去快递公司上班第一天就得到一辆变速自行车的年轻人,对爱车十分宝贝,整个人也自信了起来。
过了几年,伯乐退休了,我也把自行车送给了学生。我打从心底认同并慢慢地向老领导看齐,对待年轻的同事尽力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鼓励、关心和帮助。二十年的时光,只在弹指一挥间。不久前,老领导作为退休教师回学校参加活动。“看到、听到你不断取得进步的消息,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。”他欣慰地说道。我也向伯乐汇报起自己的近况,不自觉地又聊起刚工作时得到的那件礼物:“我的父亲走得早,都没给我留下一辆脚踏车!您教我的那些东西,我十分受用,正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年轻人呢!”
现在自行车不稀奇了,满大街都是共享单车。读书时,我有一辆“除忒铃弗响其他侪响”的老爷车,后来竟也被盗了。工作到第八个年头的夏天,我买了一辆能变速的山地自行车,骑着它沿着109国道成功抵达了拉萨。一路上,它既没掉链子,也没爆过胎,兢兢业业,保我平安,抵达目的地后我把“功成名就”的它交给物流公司寄回了上海。如今,它仍停在我们小区的车库里,偶尔陪我去感受自由的风,追逐美丽的日落。
我忘了自己是几岁学会骑自行车的了,自忖颇有天赋,无师自通地掌握了“后上车”与“前上车”。很遗憾,我的父亲没有机会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赠予什么礼物,他的影像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已变得愈发模糊,却始终与自行车“焊接”在了一起——1986年的夏天,有一次父亲下班回家时,自行车车筐里装着一个西瓜,这令全家人开心不已。我也坐过他的车横梁,安静地等待着摆渡过江。
翌年,一场意外降临。余华说,“死亡不是失去生命,而是走出了时间。”但车祸明明白白夺走了父亲的生命,也让他彻底走出了时间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蹬着自行车为生活奔忙的背影。